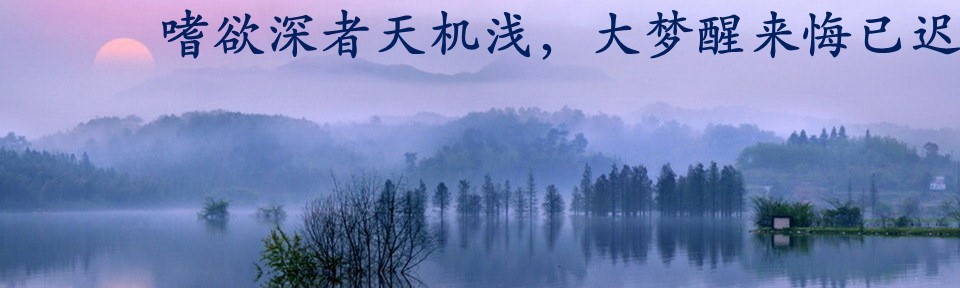自帕斯卡时代以来,许多“正统教会”中最杰出且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已普遍意识到,必须超越《圣经》的字面意义,探寻其教义与现代科学启示之间的调和之道。
威廉·劳在其著作《爱的灵性》中写道:“你们当明白,身体并非源自自身;它的一切,无论是纯净还是污秽;它的一切特质,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它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善举还是恶行,皆源于灵。我的朋友,因为在整个宇宙中,唯有灵才是真正的行动之源。而每一个灵的状态、境遇和层次,只能通过与之相应的身体状态、形式、境遇和属性得以显现,因为身体本身并无任何本性、形式、境遇或属性,除非是那创造它的灵将这些赋予它。”……
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如今以《基督教年历》(The Christian Year)一书闻名于世,在《时代论丛》(Tracts of the Times)第89期中,他阐述了一种观点,旨在为教会的教父们正名,驳斥他们因所谓的“神秘主义”而蒙受的污名。他的言辞中流露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即便并非直接源于瑞登堡的教义,也无疑深受其关于《圣经》结构原则的见解所影响。若非如此,这样的论述几乎难以出自他人之口。
“《圣经》大量使用取自自然事物的象征性语言。神圣启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始终是那种最易于接纳并吸引此类意象的语言形式,即诗意的语言。对于一个思想深邃且心怀敬畏的人来说,《圣经》中出现象征性语言这一简单事实本身,难道不是极为引人深思的吗?换言之,当圣经中的真理以可见、可感的意象呈现时,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其中的深意?《圣经》的作者正是自然的创造者。祂创造万物,使其成为现在的样貌,按祂的旨意维系它们的存在并改变它们,祂深知它们之间一切隐秘的关系、关联与特性。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当祂以某种隐喻的方式使用祂所造之物的名称来象征某种不可见的事物时,其中可能蕴含的深意远超出比喻与类比的范畴。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祂以这种方式谈论某一事物时,这一事物便超越了普通修辞和语言表达的范畴,从此具有了预表的意义。”
“这节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为自然界的作品确立了一种神秘解释的原则。诗意思维的典型意向,是从始至终将感觉到的世界视为那不可见、不可触及之物的象征;而在上帝道成肉身之前,诗歌一直是启示的既定载体。”
我们往往未曾察觉,日常语言中那些精彩的表达——即那些清晰而易于理解的言辞——其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对自然与思维之间关系及相互依存的理解。例如,当我们提及“自寻烦恼”、“命运的波折”、“人性的温情”、“固执的头脑”、“光阴似箭”、“崇高的品格”、“岁月的冷酷”、“迷迭香般的记忆(或甜美的回忆)”、“甜美的容颜”、“优雅的品味”,或是形容某人“坚如钢铁”、“冷若冰霜”、“无视自身的利益”、“对理性之声置若罔闻”,以及她拥有“清脆悦耳的声音”、“厚颜羞耻的面容”等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以或深或浅的方式解读自然界所蕴含的语言与智慧。
现代科学的最大局限在于,研究者往往将探索范围限定于可感知的现象本身——即专注于感官所能捕捉的事实,而不愿超越这些表象,去探寻其背后的神圣目的。他们不能从自然界仰望其创造者,以洞悉那些先于现象且内在于其中的意志或动因,而是将研究局限于纯粹的自然规律及现象间的关联。
倘若有人无法分辨熟人伸出的手是致意抑或攻击,我们必视其为愚钝。然而,现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较之这愚者又高明几何?他们止步于认识和命名自然之书中的字母符号,却不愿尝试解读和理解其中蕴含的更高深意旨。正因如此,世人鲜少向自然科学的信徒求索伦理或宗教的真理——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恰是自然现象所要传授给我们的真谛。终有一日,仅熟悉自然现象或精于实验者将不再被视为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必须超越物质层面,探寻灵性本源,竭力触及那神圣和谐的琴弦——正是这琴弦,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与其创造者紧密相连。
字面主义者提出异议,认为《圣经》若要成为完美的信仰准则,必须在必要之事上清晰明了,毫无疑义,无需解释;若其中存在晦涩之处,则无法作为准则或衡量标准。因此,那些超越其初始印象的更深层、更内在的含义,反而会与信仰的完美准则相矛盾。
若此说成立,为何《旧约》与《新约》之间相隔数百年之久?为何《旧约》以基督门徒中或许无人能懂的语言书写?为何《圣经》各卷皆以数百年前便已不再使用的语言记载,且多数作者的姓名及其与《圣经》的关联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依此理论,凡不精通希伯来语、科普特语、阿拉姆语或叙利亚语及希腊语者,皆无法以《圣经》为信仰准则,此等限制一经道出,其荒谬之处便昭然若揭。
为何成年人在圣言中领悟的比孩童更为深刻?为何虔诚者比世俗者更能洞察其深意?为何每位虔诚者每次阅读圣言时,总能发现新的启示?不仅如此!为何我们身处的现象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奥秘?为何我们须待圣言成为古籍后,才知晓地球绕日而非日绕地转的真理?为何指南针的发明让远海航行成为可能?为何电力成为推动文明的仆役?为何大自然这本浩瀚之书仍在不断向我们揭示新的奥秘,其震撼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往的任何发现?诚然,我们无法奢望在某一时刻,甚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完全洞悉上帝在其圣言中所蕴藏的全部真理,正如我们无法即刻参透构成我们尘世环境的上帝大能工程的所有秘密一样……
我们无法奢望仅凭字面语言便能即刻领悟上帝圣言的全部意义,正如我们无法通过自然语言瞬间洞察其深邃内涵一样。若要求人类从诞生之初便全然知晓科学逐步揭示、乃至未来可能揭示的现象世界的一切奥秘,甚至包括人类所需了解的全部真理,这与要求人类一眼洞悉《圣经》所教导的灵性世界的全部真谛一样,显得极为荒谬。正如我之前所言,来自无限上帝的信息必须适应人类灵性发展的每一个可能阶段。因此,难以想象祂会将光明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民族、阶级、时代或人间境遇。如同自然界的阳光,其光辉亦是渐次升起的,待到正午时分,光芒才得以充沛地普照大地。
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沟通对任何两个人而言,都不可能传达完全相同的内容;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两次连续的阅读中,也难以获得完全一致的理解。其教诲如同人眼的瞳孔,随着光照的强弱而扩张或收缩。而这份光明的给予与增强,其程度与速度,皆取决于我们将圣言教诲融入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唯有如此,圣言方能成为照亮我们内心的光芒。
我们可以放心地盼望,只要我们愿意善加利用,就能理解圣言的灵性或内在含义。超过这一限度的光明会被慈悲地遮蔽,以免我们亵渎它,对它要揭示的神圣真理永远视而不见,就像如果太阳的光芒没有被行星大气部分遮蔽,太阳的强光就会使我们失明一样。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被隐藏,是向那些失丧的人隐藏。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思,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是神的像。”(《哥林多后书》4:3-4)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只要我们愿意善加运用,便能领悟圣言所蕴含的灵性与内在深意。然而,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光明会被慈悲地遮掩,以防我们亵渎了它,从而对那些本应启示的神圣真理永远视而不见。这就好比,若非行星大气层对阳光的适度过滤,太阳的炽烈光芒足以令我们目盲。正如使徒保罗所言:“如果我们的福音被隐藏,是向那些失丧的人隐藏。这些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思,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哥林多后书》4:3-4)
《圣经》所蕴含的灵性真理,其高度与深度皆属无限,远非人类想象力所能企及。正如望远镜的物镜口径越大,其所能捕捉的视野便越辽阔,揭示的星辰世界也愈加丰富。同理,我们越是忠实地将《圣经》的教诲贯彻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便越能沐浴在其智慧的光芒之下,而其内在的灵性意义也将如涓涓细流,从永不枯竭的源泉中源源不断地涌现,滋养我们的心灵与生命。
我谨对多年前的忏悔稍作补充:时至今日,我仍未发现除瑞登堡及其诠释者之外的任何著作或启示,能够解答我在探寻“道即上帝”这一字面证据时所遭遇的困惑。我深信,我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千千万万在基督教国度中不断跌倒之人所经历的挑战。放眼全球所谓的基督教徒,若非葬礼或婚礼等特殊场合,真正参与教会活动、定期或偶尔遵循教会宗教仪式者,实属寥寥!终其一生,通读或聆听过《圣经》哪怕一章者,又有多少?然而,几乎每一位享有选举权的非基督徒,都会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他们看到了投票的意义,却茫然不解为何要踏入教堂。
那为他掰开的生命之粮既不美味,也无法滋养他的心灵。为何近年来理性主义在全球迅速蔓延?为何人们对达尔文、赫胥黎及其追随者的进化论和革命性学说如此狂热?为何连神职人员也频繁地将《旧约》与《新约》区别对待?为何对基督神性的怀疑日益加深?为何一些教派分崩离析,而另一些教派却用荒谬的教条来维系自身?难道不是因为神学未能跟上世界思想与灵性的进展吗?难道不是因为神职人员在阅读和解释《圣经》时,就像对待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一样,对其蕴含的深邃智慧只有最肤浅的怀疑吗?正如丁尼生所言,在当今教会的境况下,“诚实的怀疑中蕴含着更多的信仰,相信我,这信仰比坚持一半信条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