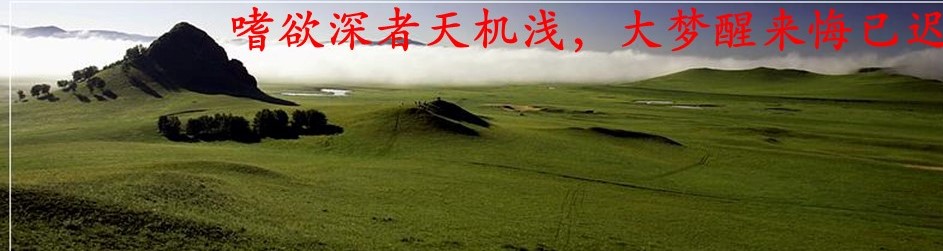我们现在回到圣托马斯酒店的餐厅。我说过,我正在读《圣经》。我从家里带来的所有可读的东西都读完了,在圣托马斯那家孤零零的书店里,所有能买到的、能读的东西也都买了、读了。事实上,我还从那里买了一本麦考利的《英格兰史》,这本书当时刚刚从伦敦出版,在我当时如饥似渴的状态下,我贪婪地阅读了它。我已经彻底逛遍了这座岛,而我的《圣经》成了我打发多余闲暇时光的唯一选择。碰巧我正在读《创世记》第12章,讲的是亚伯拉罕因饥荒被迫前往埃及的故事。当我读完后,我对克耶鲁夫先生说:“这本书被地球上最高度文明的国家接受为上帝的话语,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你听听!”于是,我读了我刚刚提到的那章的最后几节,其中讲到这位族长把他的妻子撒莱说成是他的妹妹。
“这位亚伯拉罕,”我说道,“据说是天父从世间众人中特别选出的,认为他最配得祂的恩宠;祂应许要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赐福于他,赐福给那些祝福他的人,诅咒那些诅咒他的人,并且通过他,地上的万族都将蒙福。然而,我们初次听闻他的事迹,竟是他命令妻子撒谎,这种行为无疑将她置于受辱与贬低的境地,而这一切显然只是为了让他自己免于那预期的危险——可事实却证明,这些危险不过是虚妄的臆想。‘按照我们的标准,’我问道,‘《圣经》中所描绘的那个被指为压迫上帝子民的埃及人,难道不更像是两人中品行更为高尚的那一位吗?’”
“嗯,是的,”克耶鲁夫先生回答道,“乍一看确实如此。”
“但是,”我说,“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克耶鲁夫先生似乎有意回避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是否读过瑞登堡的任何著作。我回答说,我不能说我读过,只是曾经在读法律时,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关于《婚姻之爱》的论著。但当时我认为那位朋友有点怪,所以他的推荐并没有让我对这本书产生太多好感。而且,那时我对书中讨论的主题既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能力去感兴趣,因此我对书中的内容完全没有印象,最多也只是读了很少的一部分。
“嗯,”克耶鲁夫先生说,“在《天国的奥秘》中,瑞登堡对你刚刚读的那章经文进行了阐释,也许会让你明白其中包含的内容比你想象的要多。”
我温和地表示,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清楚,我不明白别人怎么可能会对这些经文有与我不同的理解。
克耶鲁夫先生于是开始解释一些关于内义和属灵对应之类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问他是否带着他提到的那本书。他说他确实有这本书,但不确定是否随身带在酒店的行李中,他会去看看。他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带着《天国的奥秘》第一卷回来了。我发现,这本书中确实包含了rui登堡对我们刚刚讨论的经文的阐释。
(在较新的版本中,这些内容会出现在第二卷中)
我首先读了书名,书名是这样的:
《天国的奥秘》—包含在《圣经》或主的话语中的天国奥秘,从《创世记》开始展开,同时附有在灵界和天使天堂中所见的奇妙事物。译自以马内利·瑞登堡的拉丁文著作。
接着,我寻找序言,这部分通常是我最先关注的内容,但发现书中并没有序言。不过,在正文的第一页,我找到了一段类似序言的内容。内容如下:
《创世记》
《旧约》中的圣言蕴藏着天国的奥秘,字里行间无不指向主、祂的天国、教会、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然而,单从字面上理解,无人能窥见其深意。若仅以字面或字面意义来评判,人们只会将其视为犹太教会外在特征的记载。然而,每一处文字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深意,这些深意无法从表面的文字中直接察觉,唯有主曾向使徒启示并解释的少数内容例外。例如,献祭象征着主;迦南地与耶路撒冷象征着天堂,因此天堂也被称为迦南和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乐园同样承载着类似的象征意义。
然而,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最微小的部分,甚至是最细微的一笔一画,都蕴含着并体现着属灵与属天的事物。这一真理至今仍被基督教世界所深深忽视,正因如此,他们对旧约的关注显得远远不足。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思考来认识这一真理:既然圣言源于主,且属于祂,那么若其中不包含与天国、教会和信仰相关的事物,它便不可能存在。若非如此,它便不能被称作主的圣言,也无法说其中蕴藏着生命。试想:它的生命从何而来?若非源于那些属于生命的事物,即每一个细节都指向主—因为祂就是生命的本源!因此,任何在内在意义上未能聚焦于祂的事物,都是没有生命的;事实上,圣言中任何未能体现祂,或未以某种方式回归于祂的表达,都不具备神圣性。
倘若缺乏这样的生命,圣言在字面上便是死的,因为圣言与人一样。正如基督教世界所认识到的,人既有内在,也有外在。外在的人若与内在的人分离,便仅仅是一具躯壳,因而毫无生气。唯有内在的人才是活的,并将生命赋予外在的人。内在的人是外在人的灵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圣言,圣言若仅有字面上的意义,便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
只要人的思维局限于字面意义,便无法洞悉其内容所蕴含的深邃内涵。以《创世记》开篇的这几段为例:从字面意义来看,人们所能理解的仅仅是世界的创造、被称为伊甸园的乐园,以及亚当作为第一个被创造的人。谁会想到其中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含义呢?然而,这些内容中包含着迄今为止从未被揭示的奥秘,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到充分阐明—尤其是从《创世记》第一章的主题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内在意义上,它讲述的是人的重新被造,即广义上的重生,尤其是指上古教会。这一主题的呈现方式极为精妙,以至于每一个最细微的表达都蕴含着象征意义,承载着属灵的内涵,或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深邃的真理。
但是,若非从主得到启示,无人能够知晓事情的真相。因此,作为引言,可以透露的是,蒙主神圣慈悲的眷顾,我得以在过去的数年中,持续不断地与灵界的灵和天使们分享经历,聆听他们的言语,并亲自与他们交谈。由此,我得以听闻并目睹来世中令人震撼的景象,这些景象从未为世人所知,甚至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在那个世界中,我了解到各种不同的灵、死后灵魂的状态、地狱(即那些无信仰者的悲惨境遇)、天堂(即有信仰者的至福状态),以及最为重要的,整个天堂所公认的信仰教义。仰赖主的神圣慈悲,关于这些奥秘,我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
在阅读了这些引言段落之后,我翻到第12章,想一探这位蒙受殊恩的瑞典人是如何为亚伯拉罕发声的。(在较新的版本中,这部分内容收录于第二卷。)他详尽地复述了这一章的内容后,紧接着给出了题为“内在意义”的阐释,其行文风格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其内容如下:
1403. 从《创世记》第一章直到此处,或者更准确地说,直到希伯,所述的内容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虚构的历史,这些内容在内在意义上象征着属天和属灵的事物。然而,在本章随后的章节中,所述内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叙述,这些叙述的内在意义同样象征着属天和属灵的事物。只要想到这是主的圣言,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会变得清晰明白。
在这些包含真实历史叙述的章节中,每一个字句在内义上都承载着与字面意义截然不同的含义。然而,这些历史细节本身却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首先登场的人物“亚伯兰”(Abram),在整体上象征主,具体而言则代表属天之人。随后登场的人物“以撒”(Isaac),同样在整体上象征主,但具体而言则代表属灵之人。而“雅各”(Jacob),尽管在整体上也象征主,具体而言却代表属世之人。因此,他们分别象征了属于主的事物、属于祂国度的事物,以及属于教会的事物。
然而,正如前文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内义的本质在于,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超越字面意义来理解,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仿佛字面意义不存在一般;因为内义中蕴含着圣言的灵魂与生命,而这些灵魂与生命只有在字面意义仿佛“隐退”时,才能得以显现。这正是当人类阅读圣言时,天使在主引导下感知圣言的方式。
随后,瑞登堡对每节经文的内在或灵性意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几乎涵盖了该章每节经文中的每一个词,这些阐释占据了四十五页大开本的篇幅。我对他的解经理解得并不透彻,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略感失望。
我从未想过,在这本写于一百多年前、我此前从未见过的书中—在我广泛阅读英国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也极少见到对它的提及—我会发现任何可能改变或稍微修正我对亚伯拉罕或圣经看法的内容。我出于好奇而阅读,仅仅期望在读到某些内容时—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读到—会因其荒谬、不可信或不合逻辑,而让我有理由不失礼貌地将书归还给我的丹麦朋友并表示感谢。
尽管我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并不透彻,但我并未找到我所期待的东西;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自信地指出并说:“你看,你的瑞登堡要么是个傻瓜,要么是个骗子,或者两者皆是。”相反,我发现了一些奇特而引人注目的内容,这些内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例如,他对该章第一节的开篇评论让我意识到,至少我正在跟随一位深思熟虑的向导。我此前从未听过或读过类似的内容。
1408此处及后续所描述的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正如记载的那样,然而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具有象征意义,每一个词都承载着灵性的含义。这不仅适用于摩西五经,也适用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的所有历史部分,这些书卷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历史叙述。
尽管它们在字面意义上是历史叙述,但在内在意义中却隐藏着天国的奥秘。只要人的心灵仍然固执于历史细节,这些奥秘就无法被看见;只有当心灵脱离字面意义时,这些奥秘才会显现。主的圣言就像一个有着活生生灵魂的身体。只要心灵专注于身体的事物,属于灵魂的事物就不会显现,以至于人几乎不相信自己拥有灵魂,更不相信死后生命会继续。然而,一旦心灵摆脱身体的事物,属于灵魂和生命的事物就会显现;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属肉体的事物必须“死亡”,人才能重生或得以更新,也解释了为什么肉体必须死去,人才能进入天国并看见属天的事物。
2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主的话语。其“外在形式”即构成字面意义的部分,当人的心智固守于这些表面内容时,内在的深意便无从得见。然而,一旦这些外在的“躯壳”被超越或消解,内在的真义才得以首次显现。尽管如此,字面意义所依托的内容,正如人体中的物质部分一样,是通过感官进入记忆的具体事实,它们作为普通的容器,承载着内在或更深层次的真理。由此可知,容器本身与其中所蕴含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容器属于物质世界,而其内所藏则是属灵与属天的精粹。同理,圣经中的历史叙述,乃至每一句话语,都是普通的、属世的,甚至是有形的容器,其内却蕴藏着属灵与属天的奥秘。唯有透过内在意义的启示,这些深藏的真谛方能被揭示出来。
3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清晰地看出:圣经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表象,甚至是根据感官的错觉来描述的,例如说主会发怒、惩罚、诅咒、杀戮,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陈述。然而,实际上,内在的含义恰恰相反,即主从不发怒或惩罚,更不会诅咒或杀戮。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以纯诚之心相信圣经字面意义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过着仁爱的生活,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圣经所教导的无非是:每个人都应当以仁爱对待邻舍,并爱主超过一切。这样的人已经拥有了内在的真理,因此,他们会很容易摆脱由字面意思所造成的错觉。
这种观点,即圣经具有分层的含义,会随着人灵性生命的提升而逐渐变化和扩展,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这种观点将圣经与但丁或柏拉图的作品区分开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这让我觉得其中或许有些道理。但究竟是什么道理?他又是如何知道的?证据在哪里?尽管我无法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但他对前十一章与之后章节的区分—即认为旧约前十一章中关于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大洪水、巴别塔等叙述“并非真实的历史”—听起来确实有些异端,甚至近乎亵渎。
然而,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竟然有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坚持圣经的神圣起源,又不必将其创世叙述视为历史事实。因此,我并不觉得仅凭这一点就应该将瑞登堡当作异端烧死。尽管他的文章有这些可取之处,但我丝毫没有放弃,在我研究完他之前就能把他送上火刑柱的念头。我说服自己,认为他是凭借想象构建了一种神智学体系;而我也清楚地知道,人类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一种毫无破绽的体系,而这些破绽不可能完全逃过哪怕像我这样蹩脚的神学家的审视。
于是,我转向其他部分,看看书中是如何描述亚伯拉罕后来对亚比米勒的欺骗,以撒在基拉耳重复同样的欺诈行为,巴别塔的故事,夏甲的事迹,雅各和他母亲合谋骗取以扫长子名分的计策,雅各如何通过牺牲岳父拉班的利益来致富,拉结对她父亲关于神像的谎言,等等。就这样,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翻阅了整本书。其中大部分内容对我来说过于神秘,难以理解;但令我沮丧的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内容对我来说难以理解的原因,与《天体力学》对我来说难以理解的原因大致相同。虽然我遇到了许多对我来说全新且看似智慧的内容,但我并未找到任何可以让作者“出庭受审”的依据。相反,我越读越想读,这欲望随着阅读的深入而愈发强烈,并激发了我对作者本人的浓厚兴趣。
当晚,克耶鲁夫先生来吃晚饭时,我对他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研读他的朋友瑞登堡的著作,但我觉得这些作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他在世时的品格。因此,在继续深入研究他的作品之前,我希望能够了解这些方面的情况。于是,克耶鲁夫先生随即以一种颇为热情的语气,简要回顾了瑞登堡生平中的重要事件,最后他向我保证说:他怀疑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是否还能找到另一个人能够像瑞登堡那样,如此彻底地摆脱世俗、肉体和魔鬼的束缚。
我问他是否有瑞登堡的传记。他稍作思考后回答说,他记得自己的行李中有一本瑞登堡的文献集,是由纽约的一位布什先生编纂的。他说,我可以在其中找到瑞登堡同时代人的证言,这些证言是关于瑞登堡的生活非凡纯洁、品格卓越以及他完全献身于侍奉主的最好证据。我问他提到的这位布什是否是纽约大学的东方语言教授,同时也是一位长老会牧师,并且曾为圣经撰写过注释。他说,他只知道布什曾经是一名牧师,但不记得属于哪个教派,而自从接触到瑞登堡的著作后,布什便退出了原来的教派(无论是什么教派),并成为布鲁克林新教会(瑞登堡派)的牧师。
由于我早已认识布什教授,并且对他深怀敬意—无论是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都堪称卓越。因此,当我得知他竟然涉足异端学说时,不禁感到十分震惊。然而,有一点我十分确信:他绝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欺骗行为,任何以他的名义或经他认可出版的内容,其真实性都毋庸置疑。事实上,他已经彻底脱离了他从小成长的教会组织,而他在那里作为牧师和作者度过了生命中许多最美好的时光,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牺牲了在世俗眼中无疑是他的一切。这一事实让我对他所写的书以及书中的主人公愈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我恳请克耶鲁夫先生让我看看这本书。他立刻满足了我的请求。这本书名为《关于瑞登堡的文献》,主要由瑞登堡同时代人的信件和出版物组成,展示了他们对他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的依据。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放下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既惊讶又羞愧:我竟然一直对如此杰出的人物—瑞登堡的生平与工作一无所知,而书中展现的他既伟大又善良。与此同时,我却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熟悉那些根本不配为他解鞋带的人的生平。无论我之前对瑞登堡的真诚和诚信有过怎样的怀疑,这本书都彻底消除了我的疑虑。他可能曾涉入某种幻觉,但我再也不怀疑他是个骗子了。这些认识自然激发了我对他著作的更多好奇心,尤其是他的神学思想,尽管我的好奇心仍然纯粹源于智识,且仅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