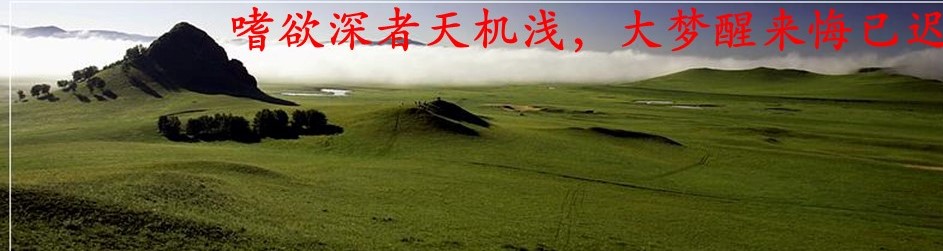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不得不提及我在圣托马斯岛冒险经历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每当回想起此事,我心中便充满满足之情,缘由众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它进一步印证了此次西印度群岛之旅中,确有一位智者在暗中指引我的方向。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必带你们进入旷野……在那里,我将与你们面对面地辩论。”(《以西结书》20:35)。
在启程前往海地的前夕,我收到来自波士顿的B.C.克拉克先生的几封介绍信,他是海地政府驻该市的领事。虽然我与克拉克先生素未谋面,但他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受到了海地政府驻纽约代表西蒙斯先生的嘱托,我曾就此次海地之行向西蒙斯先生请教过。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写给太子港商人P.B.亨特先生的。
当我们抵达港口,还未完全停泊时,一位年长的绅士乘着小船向我们驶来。他简短地向船长致意后,便转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自称是亨特先生,并告诉我克拉克先生已经提前通知他我将访问该岛,如果我在逗留期间有任何需要,他愿意随时提供帮助。我向他表示感谢,并递上了介绍信。简短交谈后——那时已近黄昏——他询问我打算在太子港何处下榻。我回答说尚未决定,计划先在船上过夜,次日早晨上岸寻找城中最佳的住处。他立即表示这样做不妥,称在港口船上过夜无异于拿生命冒险;他还补充说,太子港内没有一家酒店或寄宿处能让我满意地度过一夜,坚持我必须随他回家。在确信拒绝亨特先生的好意实属不智后,我随他前往他的住所,在太子港逗留期间一直寄居于此。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愈发感激那些促使他发出邀请的机缘,每一刻都让我对这份恩情铭记于心。
适时得知,亨特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同窗,他向我讲述了诸多关于爱默生的趣事。亨特先生虽无文学抱负,却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对海地、其公众人物及民众的了解,以及关于他们或由他们所著书籍的知识,远超我在海地或其他地方遇到的任何人;或许,他比当时任何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这些,且具备一种令人钦佩的能力,能在交谈中巧妙地传递这些信息。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似乎各方面都极为适合在其故乡取得事业成功。至于他为何离开美国前往海地,我从未冒昧探问,但有理由推测可能与某种家庭纠纷有关。他前往海地,在内陆游历了一两年,最终与太子港的一家商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我结识他之前,他已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十三年,事业相当兴旺。
除了深深感激他让我住进他家之外——若非他的帮助,我恐怕早已在抵达后的一周内,与大多数同船的伙伴们一同长眠于墓地了——我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而这份敬意,我相信他也同样真诚地回应了我。亨特先生对人生的诸多重大问题持有相当坚定的见解,且对那些著名作家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了如指掌,远胜于我当时的认知。然而,我发现他的宗教信仰,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比我的还要摇摆不定。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未来存在的状态或《圣经》的神圣起源几乎不抱任何信仰。他拥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对其中的内容如数家珍。当我回到纽约时,我深感有必要给他写一封信,详述自我们分别以来,我的一些观点所经历的深刻转变,以及促成这些转变的缘由。我还随信寄去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两三卷瑞登堡的著作,并特别向他推荐了这些书。几周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这样提及我寄去的书:
太子港,1854年4月25日。
亲爱的毕格罗先生:
我已收到您3月14日和23日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晚邮报》、瑞登堡的著作、洪堡的作品、殖民地盐业贸易报告、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药箱和顺势疗法医师手册、杂志和马鞭。对于这一切,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尤其是您寄来的瑞登堡著作。他似乎已在您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令我颇感意外。之所以意外,是因为在我们之前关于鬼魂和所谓“超自然”现象——或许那只是尚未被探索的自然现象——的随意交谈中,我发现您是一个无神论者。
瑞登堡对我来说并非全然陌生。大约十八年前,我的一批旧藏书中便有他的《天堂与地狱》和《揭秘启示录》。这些书当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世事的纷扰与追逐“财富”的诱惑未能完全抹去这些记忆,而您的善意让我得以重新拾起它们。上个星期日,我收到这些书后便开始阅读,并一直断断续续地翻阅。即便谈不上愉悦,至少它们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如同早年一样,令我的内心难以平静。
我虽无暇详细阐述我对此事的看法,但在这十八年间,我一直视瑞登堡为(自耶稣和先知以来)那些在现代能够窥见灵界、为我们提供灵界一瞥(尽管极为有限)以及那些拥有并至今仍具备第二视觉、动物磁力及相关现象能力的人们的先驱。我从未刻意结识瑞登堡的信徒,但偶然间却遇见过六位——时间跨度颇长,他们中有学者、女士、裁缝、鞋匠、学徒。每次与他们交谈后,我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纯洁的、高尚的、充满灵性的,尽管在某些心智领域并不强大,但却极富智慧。
1841年,我曾问过波士顿的一位鞋匠学徒詹姆斯·法克森:一个善良的信徒与一个善良的无信仰者有何区别?他说:“区别很大。前者因爱上帝而行善,后者因爱自己而行善。”他的话让我感到很悲伤,就像圣经中那位律法师一样。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亨特先生本就孱弱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返回美国,以便获得比海地更高水平的医疗咨询。他最终定居在费城。
据我所知,当我离开他时,他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事业中,他所处的环境中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激发他的好奇心,而瑞典堡的著作却有可能满足他。而且任何以《圣经》的神圣起源和完全默示为出发点的书籍,在试图渗透像他那样年纪和性格的不可知论者的思想时,都不得不面对诸多偏见。因此,我对他信中的语气尽管有些失望,但并不感到惊讶。同样地,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听到他提及瑞登堡,这也让我失望,却并未让我感到惊讶。
1864年春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既感到意外,又格外欣慰。信中大部分内容都与瑞登堡有关,并揭示了他思想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最好的方式便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描述。
费城,1864年3月18日
亲爱的毕格罗先生:
既然这些琐事让我有必要用这封信打扰您,我便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提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您可能还记得,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您曾从太子港寄给我几卷瑞登堡的著作,并附上了一封当时我认为相当引人深思的信。这些书包括《真实的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以及《瑞登堡生平文献》。收到这些书时,我曾翻阅过它们,后来也偶尔带着重新唤起的好奇心(因为早年我曾接触过它们)而再次阅读,有时甚至带着更直接的兴趣,但只是断断续续地读,且间隔时间往往很长。然而,这些阅读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存在,因为在最初的三四年里,每当我想到未来的生命状态时,我发现自己总是从瑞登堡的角度去看待它。
今年冬天,我的慢性病加上个人选择让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在随意阅读了一段时间后,我无意中又拿起了这些书,并一本接一本地仔细研读。书中有一些内容我尚未完全理解。例如,我未能找到关于预知与预定之间关系的满意解释,而且书中描述的灵界人物的状况,似乎过于局限于神学范畴。但总的来说,一旦接受瑞登堡是上帝指定的仆人这一前提,他的整个体系便为我提供了我所知的关于人类灵性本质和未来生命的最逻辑、最理性、最自然的解释。事实上,这是唯一一套能够让我感到信服的神学体系。
此外,瑞登堡的个人品格和生活经历也作为真理的旁证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所有其他教派创始人(包括卫斯理在内)不同,瑞登堡并不追求个人权力。他从未想过成为新组织的领袖,也不试图招募信徒。他仅仅满足于忠实地记录自己受命揭示的启示,并将建立可见教会的任务留给上帝,由祂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完成。然而,他说话时带着权威,既不争论也不回避问题,这一点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厌倦了猜测。我正在寻找他的更多著作,并必须弄清楚布什博士的讲座是否曾在《晚邮报》之外发表过。同时,我必须再次感谢您寄来的这些书,我花了十年时间才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看来,好的种子总能保存下来”……
回顾这一连串的事件,它们最终让我重拾对《圣经》的信仰,而这一切我已大致概述。我怎能不深信,自己的每一步都受到了主的指引——或许我该说,是主的意志在推动着我前行?
为何我会踏上前往海地的旅程,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引人入胜、易于抵达的未知之地等待我去探索?为何克拉克先生——一个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会心血来潮,为我撰写一封引荐信,将我引向亨特先生,而我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为何一场突如其来的热病,驱使我前往一个我毫无兴致、甚至极力回避的地方?又为何命运如此巧合,让我恰巧在那一刻抵达,而一艘驶往纽约的法国轮船因故障搁浅,加之霍乱的肆虐,使我不得不在此停留长达两三个星期,而非仅仅短暂的几个小时?
为什么克耶鲁夫先生偏偏是酒店里唯一一位我能与之建立社交联系的客人?为什么我在晨读时偶然翻到《圣经》中的一章,竟促使我向这位近乎陌生的人敞开心扉,谈论我的不可知论?为什么我能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远离一切商业的纷扰与琐碎,甚至远离书籍和报纸,让我的心灵得以休憩,直到它变得饥渴,渴望某种灵性的滋养?而就在此时,克耶鲁夫先生将瑞登堡的著作递到了我的手中?又为什么我们之后会成为同船的旅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几乎完全依赖彼此的陪伴?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我不禁自问,所有这些看似巧合的事件——如果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它们根本不会发生——除非是为了让我像雅各一样,枕着石头入睡,直到醒来时,我才恍然大悟并惊呼:“主确实在这里,而我竟未曾察觉。”从我离开纽约的那一刻起,任何一个事件——更不用说那些决定我命运的事件——如果未能成功,而我一直在试图让它们失败,那么我可能至今仍然远离《圣经》,甚至远离上帝,迷失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经历赋予了我对先知话语的深刻理解:“人不能指引自己的道路,行走的人也无法决定自己的脚步。”这一切,难道不是那只大手在悄然引导吗?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祂垂听我的呼求,转向我。
祂将我从可怕的深渊中拉出,从泥泞的沼泽中救起;
祂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健。
祂使我口唱新歌,赞美我们的神。
——《诗篇》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