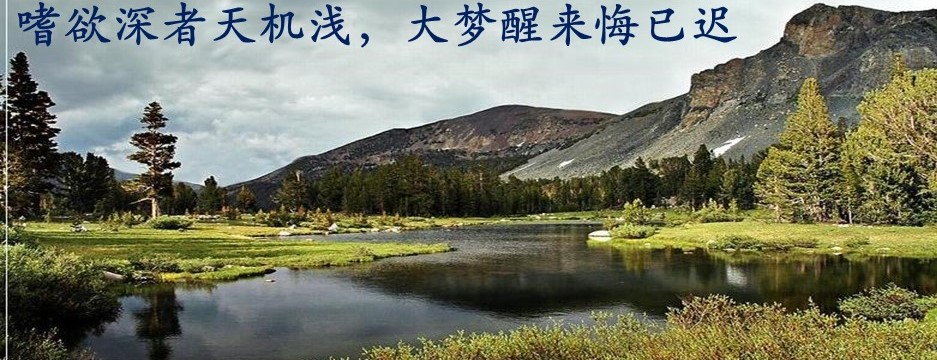尽管我逐渐被这位新朋友所吸引,但我并未忘记自己已离家甚远。原定的归期早已过去,而我自离开纽约以来,既未收到家人的音讯,也未得到商业伙伴的消息,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已得知我的近况。克耶鲁夫先生与我一同研究了圣托马斯港每艘船的目的地和航行计划,却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船只。最终,我们与一位船长展开了谈判,他指挥着一艘约130吨的前后桅横帆双桅船,该船隶属于巴尔的摩,他愿意载我们前往美国的某个港口。由于霍乱的缘故,他无法从任何西班牙港口获得预期的货物,因此他最终决定,如果我们愿意搭乘他的船,他将前往新奥尔良并在那里寻找货物。我们与他达成了协议,储备了额外的食物,并以比我之前或之后离开任何港口时更迅捷的速度,告别了圣托马斯,启程前往新奥尔良。然而,在启航之前,我恳请克耶鲁夫先生带上他所有关于瑞登堡的书籍。他非常乐意地满足了我的这一请求。
我们的航程因无风和风暴而延长,从离开圣托马斯到抵达纽约,共耗费了二十多天。在这期间,我只记得有一天——那天我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皮卡云报》的编辑带我去了庞恰特雷恩湖——除此之外,我几乎每天都会花十到十二个小时埋头研读这些著作。事实上,除了吃饭和睡觉,我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被这些书籍占据。对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很难描述这些书籍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灵性事物,尤其是对《圣经》的所有看法。
虽然我当时的状况如同福音书中那个瞎眼的人,起初只能模糊地看到人像树木般行走,但在回到家之前,我已经完全确信“这些话并非出自魔鬼附身之人”,并且瑞登堡是“一位受天国启示的学者”。对我来说,每读一行文字,都会消除一些困惑,澄清一些疑问,揭示一些奥秘,展现《圣经》中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灵性财富。即使我拥有了阿拉丁的神灯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加全神贯注,更加为我的收获而狂喜不已。
我深切体会到,曾经的我如同盲人,如今却得以看见;仿佛我的双眼睁开,看到了一个此前只能窥见其倒影或轮廓的世界。大数的扫罗在“眼睛上仿佛有鳞片掉下来,立刻恢复了视力”时所感受到的极度震惊与震撼,也无法与我在此次航程中因心灵被开启而领悟到新真理时的感受相比。在抵达新奥尔良之前,我已情不自禁地跪地呼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您帮助我。”……
当我在辛辛那提下船转乘东行的火车时,我不得不与好友克耶鲁夫和他的书籍分别。由于我需要在辛辛那提停留几个小时,我立刻前往一家书店,幸运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瑞登堡的《圣爱与圣智》和《圣治》合订本。我支付的价格让我猜测,店主并不认为这是非常珍贵的商品,但即便如此,我也绝不会用店里任何其他书来换取它。
事实上,我当时觉得除了瑞登堡的著作和《圣经》之外,我再也不会想读任何其他书籍了。在余下的旅程中,我将白天的时间全都用来阅读这份新获得的珍宝——其中的每一行文字似乎都为我在天际点亮了一颗新星。当我回到家时,虽然对于瑞登堡是否得到了特殊启示、以及这种启示的性质或程度,我的心中尚未完全明晰,也并不特别在意去了解,因为我毫不怀疑他相信自己受到了启示。此时,我不仅克服了关于基督神秘降生和神迹的所有困惑,而且对《创世记》前十二章的神圣权威也同样有了确信,而这些章节曾多次让我绊倒。如果《圣经》中有些部分关于其神圣起源的表述让我感到不够清晰,我会认为它们是为了我们的教化而赐予的,但具体基于什么权威,我并不妄加揣测,当时也不太在意。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变卖了一切去买一颗无价珍珠的人,而这笔交易如此划算,我甚至不在乎是否找回了零钱。
我一回来便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布什博士。在他那间被称为“书斋”的小房间里,我找到了他。那间屋子位于摩尔斯大楼的顶层,我曾偶尔在那里与他相遇。如今,那座大楼已被一座同名但更为宏伟的建筑所取代。房间里几乎堆满了书籍,书桌前仅留有一小块空间供他使用,旁边勉强能容纳一两位访客落座。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亲口讲述他所经历的那场心灵变革。他显得非常快乐,并且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原来,他已经从瑞登堡的教导中获益多年。在他大约184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接受瑞登堡教义与启示的理由陈述》中,他生动地描述了最初促使他特别朝这个方向研究的情况。由于这份《陈述》如今已几乎被遗忘,而他的心路历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在许多方面与我的经历颇为相似,我猜想大多数像他一样在瑞登堡那里找到解脱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在其中长大的教会对灵性上的困扰既无治愈之法,也无缓解之策。因此,我毫不怀疑,那些一直跟随我读到这里的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
(以下是布什博士《陈述》一书的部分摘录-译者)
“回首我过去五六年间在道德与认知领域的探索历程,我不得不将最初对复活这一传统教义产生质疑的那一刻,视为我真正迈向新教会的起点,尽管当时我对这一事实毫无察觉。在此之前,我对瑞登堡的思想体系并无深入了解,也未曾对他的品格作出任何理性的评判。与大多数基督徒一样,我仅满足于一种模糊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成就斐然之人,却不幸陷入了一种偏执妄想的状态,成为离奇幻觉与梦境的牺牲品——一个虽诚实却深陷于关于人死后状态以及天堂与地狱本质的最狂野幻想之中的人。”
“至于关于人性或宇宙构成的任何系统或理性的哲学,我当时宁愿在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印度教的《吠陀经》,或是我当时认为毫无意义的雅各·伯梅的狂言中去寻找,也不曾期待能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由于我只读过他作品的片段摘录,我并未准备好承认他有什么超出一位善意的神秘主义者的特质。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向世界抛出了一堆奇异混杂幻象的人,而这些幻象只可能被那些头脑中已有类似狂热倾向的人接受——这些人要么从未具备,要么早已丧失了(如果他们曾经拥有过)区分幻象与真实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他的总体评价,直到我确信当前关于“物质肉体复活”的教义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既无法通过对圣经的合理解释得到支持,也未能通过理性的公正推论得以证实。我在一本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著作(《复活论》Anastasis, etc.)中向公众阐述了我这一观点的依据。”
“我已经开始了在这座城市及其他地方的一系列公开讲座,阐述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并主张真正的复活发生在死亡之时。当我在东部城市的一场讲座结束时,一位女士偶然向我提到,我所提出的观点与瑞登堡在同一主题上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暗示她认为我一定熟悉他的著作。她这一推测并无根据,但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于是我决定首先利用一个合适的机会去了解他的思想体系,从而填补我知识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空白。”
“没过几个月,我偶然得到了一本诺布尔为支持新教会观点所著的《辩护书》(Noble’s Appeal),阅读后深受震撼。我不得不对瑞登堡及其思想体系重新作出评价。我不仅发现自己在复活本质上的总体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和阐释,并且这些观点建立在我至今仍认为坚不可摧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之上。同时,书中对主第二次降临的教义的阐述,也以一种独特的力量直击我的信念。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也对其所引用的圣经证据之丰富感到震撼。这些证据有力支持了新教会体系的核心观点。在此之前,我并未充分认识到来自圣经的证言是如此支持新教会的核心主张。直到今天,我依然毫不犹豫地认为诺布尔的《辩护书》是对这一体系的无可辩驳的辩护。”
“在此之前,我仅读过瑞登堡著作中的一些零散片段。不久之后,我得以阅读他的《天堂与地狱》。我怀着深深的敬意研读此书,但对其中所述的真实性仍持保留态度。总体而言,我倾向于承认瑞登堡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状态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感知灵性世界的现实。因为我知道,先知和使徒们也曾被赋予沉浸于那个世界的体验,这表明这种状态不仅可能存在,而且确实曾经存在过。既然它曾经存在,我认为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它就有可能再次出现;而他提出的理由,若其合理,在我看来已足够充分——我愿意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基督徒或许不会如此。
然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它彻底颠覆了我对灵性世界的所有先入之见,以至于我对他陈述的绝对可靠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不禁质疑他的感知是否足够清晰。一种疑虑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他在这一领域的先入之见是否既塑造了他的异象,又为其染上了主观的色彩。这种疑虑在他对天堂和地狱景象的描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难以想象,我们在此世熟知的物体竟会在灵性世界中“显现”出来。我不断向自己追问:“灵性的房屋、动物或鸟类究竟是何等存在?灵性的山峦、花园、树林或树木;灵性的洞穴、湖泊或溪流又是什么模样?”我从未意识到,这些事物的存在根植于人类心灵的法则,是内在灵性的迸发或流露,是其情感与思想的鲜活映射。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必然会被引入灵性现实的领域,而这些现实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瑞登堡所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它们必然是我们所称的“心灵创造”或“投射”。若稍加深入思考,我便会明白,正如后来我所领悟的那样,瑞登堡的陈述是真实的:思想虽非物质,却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对灵魂而言,唯有灵性的事物才能被称为实体,也唯有灵性的事物才能被视为真实。
事实上,在日常语言中,我们颠倒了这些术语,将物质的、能被外部感官感知的事物称为“实质的”。然而,当灵魂脱离肉体后,它便离开了已死物质的领域,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在那里,灵魂自身及其流露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或实在。因此,在灵性世界中,那些在此世被视为主观的事物,到了那里便化作了客观的现实。”
* * *
“我深知,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一观点在初次听闻时或许难以被迅速接纳,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于将心灵的表现仅仅视为行为、活动或运作。然而,让我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作出判断,看看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任何事物若非实体,又如何能够存在?若不通过其作为实体的特性和功能的展现,任何存在的事物又如何能够行动?太阳通过散发光和热来行动——难道这些光和热不是其实体的一部分吗?花朵通过散发香气来行动——难道这香气不是与花朵本身一样真实的实体吗?尽管它更加稀薄而空灵。
人的灵性亦是如此。一个人的思想和心理意象是其存在实体的外在流露;它们与其存在本身同样真实;如果一个灵魂的本体对另一个灵魂而言可以是客观现实,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他的智识概念也必然同样是客观的。因此,一个人若想被引入最辉煌的天国景象,他只需置身于那个国度中无数纯真众生天使般情感所激发的心灵创造之中。这些景象必定是美丽的,因为它们源于内在之人的道德状态,而这种状态只能通过具有相应特征的对象来呈现。它们的真实性则源于事物的本质与必然性。对灵魂而言,灵性事物必须是真实的事物。至于地狱的景象,尽管是其对立面,却同样遵循这一法则。”
“因此,当克服了与此相关的种种质疑后,我在全面接纳瑞登堡的启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意识到,这里提出的是一种关于来世主导状态的理性且哲学性的理论;然而,它显然是一种超越人类自身能力极限的启示。因此,得出的推论不仅是合理的,更是无可辩驳的:瑞登堡被引领进入一种超自然的状态,才得以揭示这一切;而承认这一点,实质上就等于承认了他主张的核心——即他声称自己获得了神圣赋权,能够揭示人类未来存在的真相,以及天堂与地狱的本质。”
“这一基本事实既已令我信服,我自然以最深的敬意倾听他从那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带来的任何其他报告;然而,我始终保持着独立判断的态度,远未盲目接受他的每一项宣告——并希望永远如此。我尚未准备好接纳他神学中的独特观点,尤其是他对“因信称义”教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这让我深感困惑。我曾被教导,这一教义是宗教改革确立的伟大信条,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正确的,仅仅因为它是那场斗争的结果——那场常被称为从教皇制度谬误中挣脱的‘光荣革新’。”
“我尚未意识到,宗教改革中的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革新。同样,在理解赎罪真正本质的独特观点上,我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赎罪的真正意义与“唯信称义”的主流教义密不可分。直到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后,我才得以全面接纳如今在我看来新教会在这一问题上更符合《圣经》的观点——即赎罪的含义正如这个词所揭示的:和解——是上帝使世界与祂和解,而非祂与世界和解。”
“然而,最令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圣经》的内在或灵性意义。我深信,即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真理,瑞登堡的解释也将其推向了完全幻想的极端。我几乎毫不怀疑,即便我有朝一日接受这一体系,也会在这方面有所保留。任何对这一总体框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立刻看出,我当时尚未领悟“对应学”的真正精髓——这一学说正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并必然从中衍生出其他内容。然而,随着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的灵性本质,以及一个根本事实——即所有尘世事物都因灵性力量的流入而被赋予活力、被塑造、被激活——这一学科的真理逐渐在我眼前显现得愈发清晰。”
后来,我与布什博士进行了多次愉快而富有启发的交谈。我很快购买了一套《天国的奥秘》,以及瑞登堡的其他神学著作,因为我深感需要它们。我还找到了位于三十五街的教堂,那里主要是瑞登堡著作的研究者们常去的地方,当时由乔希·吉尔斯牧师主持布道。自那以后,只要我在城里,便会习惯性地前往那里参加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