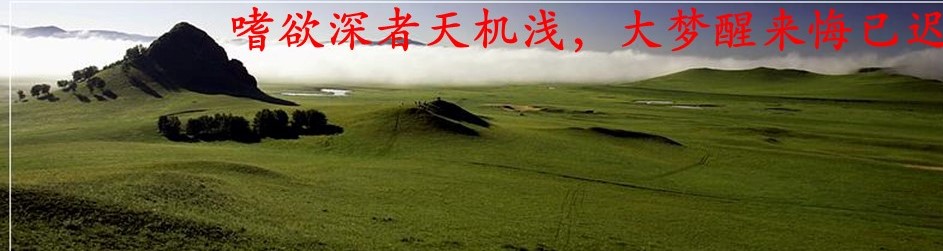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的父母都是长老会教徒,他们继承了长老会的传统并对此坚信,而我从小便被按照这一教派最严格的方式抚养长大。然而,在我十一岁那年,我被送到了寄宿学校,此后除了学校和规定假期外,我再也没有机会与父母一起在家生活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很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根据自己有限的见识,对比讲坛上听到的以及圣经中读到的内容,从逻辑和神学的角度进行判断。我无法断定这是“堕落”还是“提升”。
我很早就开始察觉到圣经中一些在我看来前后矛盾或不太可能的地方。随着我的成长,这些问题的数量不断增加,而这种增长速度加快的原因之一是,我的灵性导师大多未能让我感受到他们是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或是负有特殊使命向饥渴的灵魂分授生命之饼。讲坛上的逻辑谬误和宗派诡辩无疑容易助长一种倾向,即质疑同一来源的一切内容的真实性。我确实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此外,年轻人在发现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更聪明或更优秀之人的错误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感到惬意。因此,在虚荣心和诚恳的怀疑之间,我恐怕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我认为圣经中的矛盾之处,而不是去寻找那些可能有益于塑造我的品性、指导我日常言行的东西。
根据当时讲道所提供的微光,我无法理解为何上帝对祂独生子的爱会少于对因罪而被定罪的世人;也难以明白,某人的死,尤其是一个无辜者的死,如何能使恶人更适合进入天堂;更不理解,上帝怎能从祂无辜子孙的受苦中获得任何满足。此外,如果基督的死是为了赎世人的罪,那么在祂完成赎罪之死后,为何仍有罪人需要为后来所犯的罪负责?既然世人的罪已被赎清,岂不意味着代价已经妥善支付?而且,我也完全不明白,既然基督知道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将复活,并重新坐在父的右边,祂的死又如何能被视为无限的牺牲?
从幼年起,我便习惯复述主推荐给门徒的祷告词,其中请求父“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然而,当我读到《雅各书》中说“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时,我对这一祷告的恰当性感到困惑。这似乎隐含着对上帝的责备,而《雅各书》却明明告诉我们,连怀疑祂会这样做都是有罪的。
摩西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同样充满了疑难。我徒劳地试图调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太阳是地球上一切光的来源——与《创世记》的记载之间的矛盾。根据《创世记》,光的创造发生在第一日,植物的创造发生在第三日,而太阳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然而,显然没有太阳就既不会有光,也不会有植物。此外,在太阳尚未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日”又如何能够如记载中所描述的那样分为早晨和晚上呢?
当我发现圣经的支持者声称可以将摩西所述的“创世日”解释为并非二十四小时的一天,而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以试图将6000年的创造理论与地质学知识调和时,我不禁推测,他们不过是试图摆脱一个荒谬的理论,却陷入了更大的荒谬之中。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第七日—即“上帝从祂所做的一切工作中安息”的那一天—也必然和之前的任何一天一样漫长。
我的这种嗜好,就是猎取和追寻那些在我看来不协调、不一致或无关紧要的圣言经文,这种嗜好因其所吸食的东西而滋长。如今回想起那段时间,我感到羞愧和痛苦,因为我竟是如此盲目和愚蠢,却还自以为是在从事有益的工作。
大约在1842年,我刚获得律师资格后不久,因机缘巧合与一位在律师界颇有声望的律师建立了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他后来担任了本州最高司法职位之一。他比我年长十二到十四岁,对我产生了好感,这一点至今我仍未完全明白,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具备一种不寻常的能力,能够包容他人的怪癖,而我们之间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我敬佩他的才华和刚毅的品格,也乐于倾听他的谈话——尽管这些谈话有时略显挑剔,甚至可以说带些苛刻,但却总是妙趣横生,且往往颇具启发性,尤其对我这样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多年来,我们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并在同一家酒店用餐。在搬到纽约定居之前,他曾深受当时尚属新颖的高尔(Gall)和斯珀兹海姆(Spurzheim)学说的吸引,还与几位绅士一道联合邀请爱丁堡的康贝博士(Dr. Combe)前往美国讲解他们的新学科。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学派的哲学观点,并逐渐倾向于宿命论,甚至否认道德责任。他认为,决定一个人行为和品格的关键因素是颅骨发育,而非意志。正是这一观点最终使他拒绝承认意志能够摆脱生理结构的约束或决定性影响。
他的父母并未培养他对《圣经》的敬畏或对教会及神职人员的尊重。当我与他相识时,他常将这本神圣的书称作“剃刀皮条”(即磨快剃刀的皮革条),因为在他和他早年的许多朋友看来,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有用的用途。尽管他对《圣经》毫无敬畏,且很少走进教堂,他却是一个显著有良知的人。他的品德在世俗层面上的发展,比我当时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充分且完整。在评判人或行为时,他习惯以伦理(而非灵性)状况作为决定性标准。他谈吐不凡,常常妙语连珠,而他用“光谱分析”般的方法剖析人类行为动机的方式,对我而言既新颖又在某些方面极具启发性。不幸的是,这些方法使我心中慢慢萌芽的怀疑焕发了新的活力:我未能理解的《圣经》内容是《圣经》的缺陷,而非我自己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愈发强烈,尽管我所接受的宗教观念并未迅速崩塌。我无法确切指出,是哪一件事或哪个时刻使我对启示宗教的信仰开始有意识地减弱;也无法说清,在我的灵性地平线上,太阳何时停驻在基遍,月亮何时静止于亚雅仑谷。我随波逐流,那暗藏的力量与方向从未引起我的注意,更未占据我的思绪,直至我发现自己正逐渐驶向不信之海的辽阔水域。
在我访问圣托马斯时,我想我几乎已经不再将《圣经》视为比马可斯·奥勒留或孔子的著作更具权威的作品了,唯一的例外是它教导了一种更崇高且更全面的道德体系。至于拿撒勒人耶稣,我认为他或许是最优秀的人之一——如果他确实存在的话,但对此我并不十分确定。至于他的道成肉身、神迹和复活,我时常心存疑虑。我倾向于将这些归类为类似于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的传说。我也毫不犹豫地问自己:“这不就是那木匠、马利亚的儿子、雅各、犹大和西门的兄弟吗?”如果我参加任何教会活动,通常会选择一神论派的教堂,而目的更多是为了寻求文学上的启发,而非灵性上的滋养。
我对《旧约》的看法,大致与科布登曾对我表达的看法相似:它是一部为犹太人而写的书,与我们无关。我曾以为自己确实是这么看的,但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对它进行过多少深入的思考;又或者,我对《圣经》神圣起源的怀疑,只是表面现象,出现在身体和心智快速成长的阶段,而我幼年时所受的更深刻的教诲与训练,则在内心深处暂时沉睡。即便在那个时期,我也从未对《圣经》表现出冷漠或不敬;每当听到有人以亵渎的方式谈论它,我都会感到不快。至于这种感受的来源或原因,当时我毫无头绪。或许,如果有人逼迫我去解释或捍卫这种感受,我可能会像彼得一样,选择否认它。我想,在这方面,我的经历并不罕见……
尽管我对《圣经》存有许多批判性的困惑,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书架上最有趣的一本书。即使在我不再因更高的目的而翻阅它之后,我依然频繁地阅读它。正如希律王敬畏约翰,因知道他公义且圣洁,并乐于倾听他的教诲一样,我或许也怀有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因为我深知它公正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神圣的。尽管我抱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我依然阅读它,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异教徒的兴趣罢了。